我的朋友小柔,是一個非常出色的視覺設計師,
每次完成的作品都讓客戶讚譽有加,也受到公司的器重。
然而,我發現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:
每當別人稱讚她的作品時,她的表情會變得有些僵硬,
語氣也總是帶著一絲不自然。
她會習慣性地說:
「沒有啦,還好而已,這個地方還可以更好。」
你可能會覺得這是謙虛,但認識她那麼多年,
我能感受到那並不是社交上的客套,而是一種本能的抗拒。
至於抗拒什麼,我並不了解。
直到有一次看到她與小孩的互動,
我才懂得無法收下稱讚的背後故事。
不符合期待的粉紅大象
那次我們約在她家裡聚會,吃著喜歡的外賣、更新彼此的生活進度。
聊著聊著,在一旁畫畫的孩子拿著剛完成的作品,
興奮地邊跑邊說:
「媽咪媽咪,你看你看,我畫的大象!」
孩子高興地補充道:「媽咪,我的大象是粉紅色的!」
小柔低頭看了一眼,語氣平淡地說:
「粉紅色的大象?你看過大象是粉紅色的嗎?」
孩子臉上的笑容瞬間凝結,小小的腦袋瓜似乎無法理解這樣的問題。
他張了嘴,欲言又止,最後默默地把畫收了起來回到房間。
小柔看著小孩的背影似乎心裡泛起一些漣漪,我有些不解。
那天聊得有點晚,孩子睡著後,我們開了瓶紅酒繼續坐在陽台聊天。
夜風輕拂,我們安靜地喝著酒,看著星空。
不幸的人用一生治癒童年?
突然,小柔開口道:
『你有聽過不幸的人用一生治癒童年嗎?』接著,她緩緩道出兒時的經歷。
小柔的父親是長年在外工作,家裡只有她和母親。
自有印象以來,家裡總被打掃得一塵不染,母親話不多,總在忙著做各種手工藝。
記得有一次,她興奮地向母親展示在學校獲獎的畫作,
母親抬頭看了一眼,便再低頭繼續忙於手上的編織,這樣的情況也發生在日常對話中。
當小柔分享在學校的日常趣事時,母親總是面無表情,不給任何回應。
那時候的她,內心悄悄長出一個聲音:
『一定是我不夠好,不夠努力,我不值得被看見。』
為了證明自己的價值,她學會了一種自我保護的方式:挑剔。
她相信,只有不斷地「成為更好的自己」,才有值得被稱讚的資格。
這樣的信念,慢慢地變成了她對對完美的執著
以及與世界的相處模式。
她無法看見孩子畫作裡的創意與童趣,
在她只有足夠優秀才值得被看見;
她無法真心接受別人的讚美,
因此她總能在作品中找到無數個可以更好的地方。
對她而言,只有足夠優秀,才值得被稱讚。
小柔深信,只有持續的批判和挑剔,才能讓自己不斷進步。
就這樣,她用這種方式活到了40多歲。
聽著小柔的童年經歷,逐漸理解她無法說出口的稱讚的源頭。
「那…現在的妳治癒自己了嗎?」我問。
小柔看著星空沒有回答,眼眶開始泛淚。
沈默良久,她緩緩將酒杯舉向星空,
彷彿在敬一個遠方的誰,也像是在對話。
看著她的眼淚滑過臉頰,我們都沒有說話。
或許,有些傷痕永遠無法被治癒。
然而,它們可能不會再像從前那樣劇烈疼痛,卻以另一種方式持續存在,
並影響著我們的每一個決定。
就像小柔無法收下稱讚、下意識地挑剔,
是一種長久以來,為了保護自己而形成的生存模式。
它幫我們隔絕了童年的脆弱,但也同時阻擋了我們感受溫暖的能力。
我們或多或少都帶著童年的影子在生活,那些來不及說出口的稱讚,
來不及被看見的渴望,都成了我們與世界相處的方式。
我們習慣了用批判來鞭策自己,用完美來證明價值;
我們深信,只有「夠好」,才值得被愛。
長大後的我們,已不再是那個無助地等著大人給予肯定的孩子。
小時候想要的肯定與安慰,也許此時此刻的我們,也能夠給自己。
為自己撐傘
那天過後,我們各自回到生活。
某天,手機傳來一則訊息,是小柔傳來一張圖片。
是那天小孩的畫作,粉紅象旁多了一隻粉色企鵝。
那隻企鵝對大象說:「I Love You。」
小柔沒有多說什麼,但那隻粉紅色的企鵝,就像是在表達:
我們看起來不符合別人的期待,但我們仍值得被愛。
因為這樣的你,已經足夠好了。
寫在最後,
童年的傷痕就像是一場下不停的雨,
小時候沒有能力保護自己,所以總被全身淋濕。
但長大後的你,已經擁有了為自己撐傘的能力。
這把傘,或許是我們懂得與自己和解的那份溫柔,
或許是我們勇敢對內心小孩說「你已經夠好了」的那個擁抱。
我們無法阻止雨的來臨,但我們可以決定,不再讓自己淋濕。
祝好,
Cerys
【延伸閱讀】
▶︎ 啟動內在小孩的自我療癒,讓你收穫幸福人生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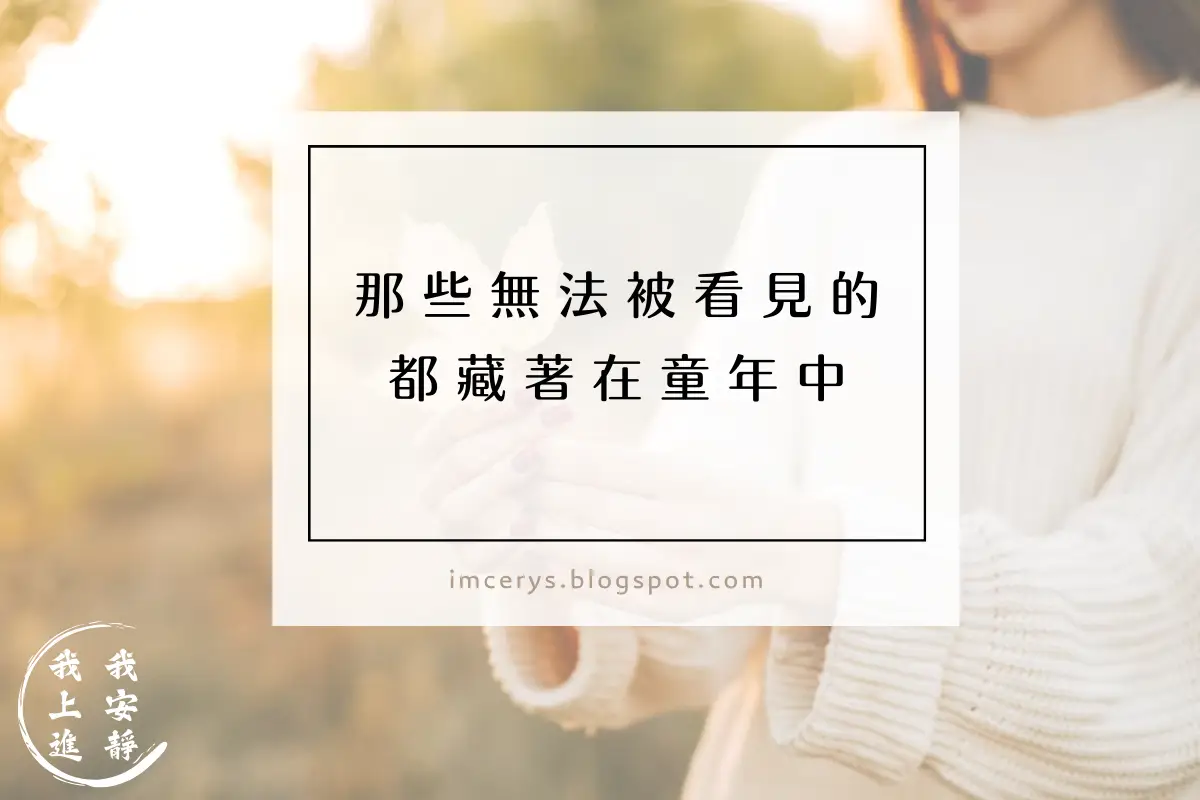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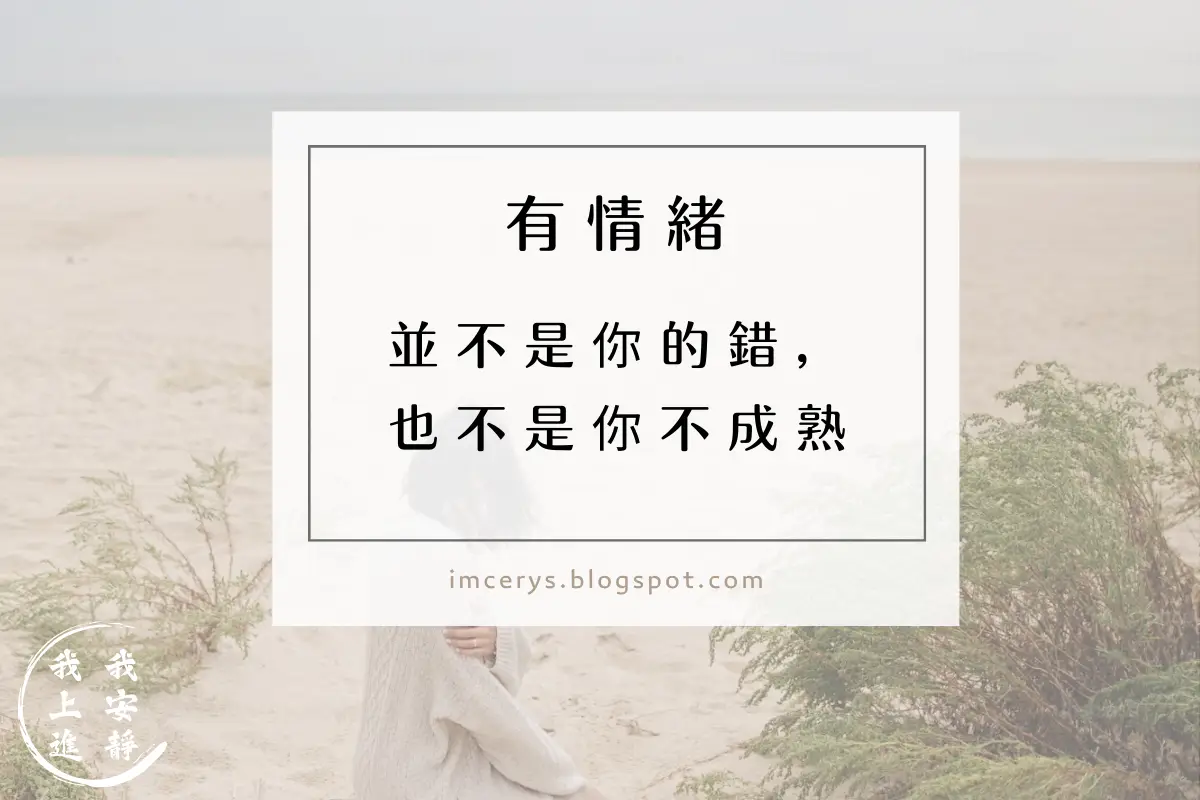
0 留言